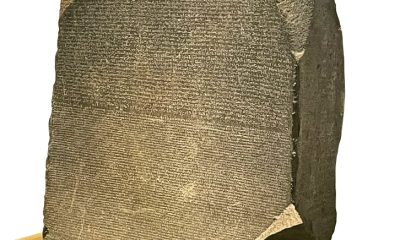副刊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試當真》Channel需要執

【明報專訊】早晨!創業5年的香港YouTube頻道《試當真》今日正式執笠。大半年前,他們在愚人節率先預告這個消息;20日前,又以一場自嘲食字的「白金像獎」典禮喪事喜辦,延續一貫風格。蓋棺《試當真》,「好青年荼毒室」豬文形容這5年是「借來的時光」。向誰借不得而知,借了什麼不太確定,只知道「借咗要還」,當一切被「收返」後,我們再留不住時光。
(告別訪問二之二)
借了什麼不太確定,Channel需要過女、錢、橋……偽紀錄片(Mockumentary)式的「Channel需要」系列,是他們創作一大特色。影評人查柏朗認為,此系列每次更新都標誌着《試》的一個階段。偽紀錄片裏真真假假,但如今Channel需要執,這5年的成長卻無比真實。
試吓成長
「白金像獎」最佳編劇《大人棍》,探討的正是成長的幾堂課。第一課,是自信與認識自己。被譽為《試》「第四人」的梁顥晉(火柴),在團隊中負責拍攝,逾千條影片由他操刀。他回想,剛畢業時拍攝經驗寥寥,游學修卻讓他一同參與首部短劇《寫實的天能》的拍攝,讓他慢慢學習,多年來由「細機變大機」,「讓我慢慢開始學到怎樣和行內接觸」。
透過「編劇試當真」加入團隊的盧嘉誼(Ellen)也有同樣感覺,認為這5年對所有人而言,都是一段學習過程,「以前會質疑為什麼一定要跟某些規則?但久而久之,再回望就覺得是有原因」。她形容:「大家雖然慢慢在成長中和整個影視行業接軌,但同時都摸(索)了一套屬於自己的風格。」
憶起當初膽粗粗投稿,Ellen說當時並無太大自信,但「摸吓摸吓」後,她現在已被視為團隊不可或缺的要員,多條精彩短劇皆出自她手筆,「無論是同事、老闆和觀眾都給予我很大信心,原來我都可以自己去度橋、去拍片。雖然拍攝時很多跌跌撞撞,但到最後原來總有方法令影片『見得吓人』」。成長中難免犯錯,《試》這個實驗工場讓他們有空間trial and error,好好認識自己,好好想想還有什麼要認識。
試吓告別
然後我們會認識到這個世界,明白世上有些事可以控制,有些事無法控制,例如死亡。於是我們學會妥協,學會告別。接受生離死別,是《大人棍》中關於成長最難的一課。只是在這個流行離開的時代,很多人都不擅長說再見。時代的更迭往往令人措手不及,我們還來不及告別,就被捲入下一個浪潮,下一個我們沒有話語權的時代。
《試》就選擇提前半年和大家好好道別。有始有終,何嘗不是一種自由?蘇豪坦言,執笠或許正是因為太過自由,「有時候大家會放下日常工作,參與感興趣的項目,然後才做回routine」。游學修也分享,拍廣告那些吃力不討好的工作,通常無人認頭,最後永遠只有幾個人「硬食」。
「豪腎修」曾輪流揸旗公司營運,但要兼顧創作、管理及各樣事務,根本分身不暇。蘇豪形容:「拍電影會有一段時間進入『精神時間房』,chur足幾個月,但我們好像5年都是這樣。」團隊成員都深明,各自都有藝術家性格和執著,難免會有摩擦和不快。頻道經歷過低潮,試過休息,也試過不同方法,但問題日積月累,始終沒有完美答案。
Channel需要過女、錢、橋……但最需要的,其實是管理。
「因管理不善而在YouTube排名節節下跌的《試當真》」未有寫在結業通告中,但游學修認同這是事實,「我承認做老闆不是很成功,在公司決策、營運、內部運作上,有很多東西應該要做好一點。或者我沒有這個能力,也可能真的沒有這個時間和空間」。但若撇除生意角度,他難言失敗:「如果現在結業是一個失敗,我覺得這個失敗造就了當中很多成功……如果不是這樣走,或者我們可以避免結業,但當中有很多成功不會出現。」
他解釋,所謂的成功和失敗是環環相扣,譬如大家的自由自在,就衍生了很多出色的作品,但也是其中一個走不下去的原因,「我們借了一樣東西燃燒了5年,生了一些很聰明、無見過的想法,但同時這種燃燒會殆盡」。5年時間不長也不短,公司內部也一直半開玩笑說會執笠,許賢說:「每件事都有一個周期,加上剛剛提到的這些局面,既然有一種很辛苦才營運到的感覺,執笠反而會好一點。」
也難怪他們會說,在預告收皮後有種如釋重負的感覺,雖不捨但不會後悔。蘇豪感喟:「這5年就像和這群人一起經歷了一場夢。一時在演出、一時在度橋、一時在覆客戶電話、一時又在扮豪媽媽……真的好像在做夢一樣,經歷了『好跳』的精神狀態。」他頓了頓,說:「但最後我覺得,依然是一個美夢。」
Channel需要唞
有過美滿旅程,但時間夠了,還是要夢醒張開眼睛。或許《試當真(暫名)》的命名早已命定了一切,永遠掛着的「暫名」二字的枷鎖,代表的除了是不同可能和面向,也代表着那借來的暫時和不確定。但執笠不一定代表終結,曾多次揚言要走的吳兆麟(Nero)形容:「『執』的意思是四處去看一看、回一回氣,讓大局走一走,讓子彈飛一輪,看看下一個世代,再想想怎樣做。」
但Nero擔憂,下一代的品味會完全和香港共同回憶脫節。他分享,創作時偶爾也會感到文化斷層,「豪腎其實就是軟硬,軟硬沒聽過?即是艾粒,艾粒都沒聽過?那快慢必呢?知道為什麼兩個都要坐(監)嗎?不知道」。他解釋,有些典故和「梗」過去明明通用,但到「00年那代後」好像突然停了,「公司有年輕人連彭定康是誰都不知道……他們可能真的無必要知道,但肥彭食蛋撻,是我們共同的香港文化吧」。
再見有時,聚散有時,時代浪潮或許不可逆,但《大人棍》有一課,叫「能力愈大,責任愈大」,坐擁60多萬訂閱的《試》,這幾年搞過校花校草提拔新人,收台前又舉辦短片大賽,讓不少創作者被看見。Nero笑言,他們就如「文化中間人」承先啟後,但其實他們的創作並無刻意尋求下一代共鳴,只是在呈現「我們這代人吸收什麼」,推廣他們認為美好的事物,「當下一代對我們的事物也感興趣時,大家便擁有一個共同語言,表達到他們的共鳴」。
《大人棍》最後一幕,無聲無息地交棒到下一代,讓他們揮灑自如。《試當真》在風光大葬前,借用了前朝四代香港人留下的共同語言,向下一代借用了他們的網絡空間,在知道的大限將至前,說出這代香港人由青春到妥協。
借來的時光要還,留不住,留得住的,是一段屬於他們的香港製造。
文˙凌俊賢、胡戩、鄭樂恒
…………………………………
人類不宜飛行?
10年前,游學修在電影《哪一天我們會飛》裏飾演追夢少年,許賢和蘇豪在《CapTV》埋頭創作;10年後,他們創立的《試當真》在5年旅程後悄然落幕。但結束從來不是終點,在早前的「試當真白金像獎」台上,游學修點名後起之秀《梁育傳媒》,叫他們生生性性。這群二十出頭的年輕人,上傳的第一條短劇就叫做《人類不宜飛行》,講面對打壓,作為非主流「仍然要相信這裏會有想像」。
《梁育傳媒》是「試當真喜劇大短片比賽」學生組冠軍,由危志樂(危險)、阮偉豪(豪仔)、楊皓森(Foster)和梁育銓組成。若不是《試當真》的比賽,4名年輕人或許早已在現實面前各奔東西。梁育銓3年前參加「校花校草」落選後成了打工仔;一心想做YouTuber的Foster因學業成績欠佳而轉學科;危險和豪仔雖學拍片卻始終苦無機會。豪仔慨嘆:「如果90年代時我正值壯年,機會應該很多吧?但現在不一樣了。」
被看見的新面孔
5年前「豪腎修」正是覺得這一代不被看見,才創立《試當真》。5年間,他們透過不同計劃,讓更多新面孔被看見。《梁育傳媒》4人坦言:「若沒有這個比賽,能被看見的渠道實在太少,讓我們多了一個改變方向的選擇。」
訪問間4人顯得生澀拘謹,怯生生地問:「我們是不是很kick?」隨即又急着解釋:「但我們是真心這樣,不是裝的。」有人形容他們很像「豪腎」,散發着鬆弛慵懶的氛圍和默契,作品又常在無厘頭中藏着批判與思考。危險說:「我們雖然嘻皮笑臉,但如果香港有多一些像我們這樣的人,社會或許不會那麼繃緊。」或許太過理想,但他們仍願在可行的空間裏,以不同方式和幽默回應現實,「就像《試當真》一樣」。
感染不同世代創作人
《試當真》的能量也感染了不同世代的創作人。憑《年少日記》獲金像獎新晉導演的卓亦謙,在「白金像獎」上稱《試當真》是他的動力。在行業打滾多年的廖銘賢(Stan)是「試當真喜劇大短片比賽」公開組冠軍,他形容,能以這種方式成為他們歷史的一部分,別具意義。比賽亦讓他認識很多「有火」的創作人,燃起他創作初心,「大家都是因為愛才留在這個行業。既然大家仍選擇留在香港,就只能一起樂觀面對」。
那麼,《梁育傳媒》會想成為「試當真2.0」,還是仿效另一網台《JFFT》4子做直播?他們笑說:「不會複製他們風格,但可以繼承他們的精神和粉絲!我們要做自己,帶着那份『試吓認真』的態度走下去。」採訪尾聲,他們又開始天馬行空:「以後要做到百老匯電影中心1號院、2號院都有我們的戲!」
「為什麼不是4套?」
「還是在巴倫紐?」
「一個康城、一個柏林!」
這裏還適宜飛行嗎?至少,仍有一群人願意走上前人的路,相信這裏會有想像。
文˙凌俊賢
…………………………………
海外粉絲看《試當真》跌碰
看見香港身分連結
兩年前,《試當真》團隊在溫哥華舉行粉絲見面會,記者當時訪問過的忠實「認真毛」不約而同提到:《試當真》不止是一個頻道,更是一種陪伴。它將社會現象與關懷化為嬉笑怒罵,記錄當下香港的情緒與狀態,回望亦不覺過時。
移居美加30年的「認真毛」ET說,如今香港看似失去希望,但《試》卻展現出一種堅持,「在無力中尋找力量,讓人覺得這裏仍有希望」。在移民世代中,《試》那些如游學修口中自嘲的「戇╳」跌碰,都曾經令出走的港人可在他鄉尋回文化身分連結。
ET也表示,過去在美國缺乏香港人網絡,而《試》作為香港YouTube「大台」,帶動了整個界別,讓她重新接觸香港文化,甚至曾組織粉絲到機場拉橫額接機,「我真的不是瘋狂fans!偶像外訪這麼大件事,竟然無人行動!」
ET從洛杉磯搬回溫哥華後,因YouTube演算法推薦認識了《試當真》,見識到那種港式耐人尋味、「山寨」的粗糙製作、幽默及扭橋,「好像『撞邪』,被落了降頭」,「《試當真》不是用一個正常的途徑去發信息予你,那些耐人尋味的twist、幽默要你『諗一諗』,思考一下後更深深記得劇情」。
運用念力凡人亦可以飛
居於巴黎的八十後Roy認為,在2021年的時空下,《試》將香港社會問題以娛樂方式呈現,「香港是一個充滿回憶、人和事的地方,跟我有非常深厚連結,以及define(定義)到自己的地方」。香港或然是一種文化密碼(Cultural Code),各種生活「inside joke」令信息傳遞有一定入場門檻,「我們一同經歷過運動及疫情,大家很多想法是……大家會明白,不需要從《試》口中得知,在身邊家人朋友間,很多事情已經可在腦內補完」。
ET坦言,在美加難以向同輩推介《試》,只有新移民港人才有共感。「不會再有頻道拍出這種片——創作人需要空間,太多掣肘不如不創作。」她早已預見,香港的環境是「執笠」之因;Roy則認為,或許不是《試》做得不好,而是大環境改變,是創作者都去到人生「好kick」階段。但他心忖,只要夠膽嘗試,實驗性甚強的作品仍會予人能量。《試》已經成功影響過自己,有些想法幫到自己,或就是其意義。如果頻道作品不會如《CapTV》般被清空,對未來的創作者必然「音容宛在」。
去到一個階段都要試吓執笠
Channel終於執,ET曾擔心頻道結束後,自己會對香港文化逐漸冷淡,但《試》以特別方式開拓了她的眼界,甚至讓她為香港人身分自豪,「我走了這麼久,認識的香港人大都在專心掙錢,這些都不會令我自豪。但是2019年、2020年之後……我真的覺得香港人是有能力,原來有很多人是重視創作,有群人是關心社會」。
Roy則將「執笠」理解為創作團隊去到一個生命階段「都要試吓執笠」。香港人需要理解自己的轉變,尋求的安慰大概如此。
或許香港從來都係試吓就當咗真,衝過去,頂多也就塞在駿業里。
文˙鄭樂恒
■答•《試當真》
YouTube頻道,生於2020年10月26日,卒於2025年10月26日。認真試吓,試吓認真,今次試吓執笠
■答•《梁育傳媒》
成員包括場務銓、茶水豪、場記樂、道具森
■答•廖銘賢
導演,「試當真喜劇大短片比賽」公開組冠軍
■問•凌俊賢
自由記者,書寫香港
■問•胡戩
立命館大學國際關係學碩士
■問•鄭樂恒
自由記者,研究香港流行文化、離散媒體、身分認同,走遍加拿大、英國、台灣,未知去邊度。在大興北成長,每次見到在輕鐵月台拍片都笑到失控
編輯˙王翠麗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