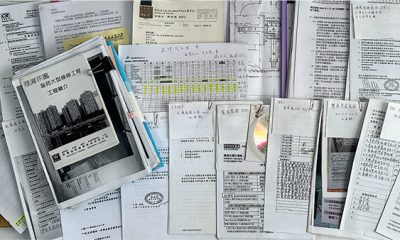副刊
通識導賞:扎根香港地 25載種子試驗田

【明報專訊】黃竹坑南臨海風、北倚山脊,曾有港島少見的農業用地:田畦連着魚塘,豬舍貼着菜圃,供應香港地的三餐。鄉里又分「新圍」、「舊圍」。相傳1841年英軍自水坑口上岸,問村名,答曰「香港圍」,香港之名遂廣為流傳。傳說未必確鑿,但此地確實曾是港島的菜籃子與記憶庫。上世紀30年代以後,伴隨都市化發展,浸水養蚊諸多不便,此地水稻逐步轉向旱地作物。再往後,海洋公園圈起山與海灣,香港仔隧道與南港島線相繼通車,大片農地逐步退場,僅餘小部分延續至今,1929年創立的高華花園便是其中之一。從自給農業到「中轉貿易」,再到「本地研發、重心外移」,它見證了香港農業的變遷,也延續那份對土地的執著。
微時間線
1840s:
港島南面(香港仔一帶)成為艦隊停泊補給港口
1950s – 70s:
黃竹坑山谷廣泛種菜、養豬;南區供應港島廚房
1970s後期 – 80s:
海洋公園建成、香港仔隧道通車,大片農地被收回改作基建與房地產
1997 – 2000s:
高華將主力由貿易轉為育種
2010s後:
本地園區多數因人手與成本問題停耕;高華將研發與試驗移往新界、中國內地(廣東、雲南)、台灣及泰國等地
種菜賣花 什麼也做過
本地農業育種專家、高華種子負責人謝天佑憶事過境遷、學農往事,總是語氣平淡。原先他旁觀並協助父輩打理園圃,自小與高華的園地建立連結。後來,原是為興趣購置的自留地隨着家業變遷,逐漸承擔起維生盈利的功用,他中學畢業後,赴美修讀農學。
回憶70年代中自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植物生理學博士畢業的情形,「那時以色列和阿拉伯打仗,油價又升,經濟蕭條,美國本地保護主義加上石油危機,經濟滯脹同時教職銳減」,與當下時局有幾分相似。最終,他決定回流香港,在嘉道理農場做過半年,隨後接手父親留下的高華花園。「那時候回來要生存,我們什麼都做過。種菜、賣菜、賣花、賣貨,拿去街邊走鬼檔,還差點被差佬抓。」記者好奇問,莫非要謝博士親自去街頭賣自家花卉,「那時候,還有誰幫我?」謝反問。
沒有牌照制度的年代,種了花便帶去臨街擺檔,差佬不趕就算好運。不過他直言:「其實,一直都想重做種子,覺得種子的潛力大。」 這句話放到今天像是回顧的總結,但對70年代的他而言則是尚未展開的伏筆,逐漸將專業所學與自家土地重新連起。「後來大陸逐步開放,市場是很宏大,香港有幾家公司已經在菜種生意深耕多年。」最初轉投種子貿易,正值他的美國朋友需要在亞洲製番茄種,原本在台灣設基地,隨經濟起飛、人工高昂,不得不另尋成本更低的地方。番茄製種屬典型的勞動密集產業,他便因緣際會幫忙把項目推向大陸,也隨之深入種子貿易,美國、日本、歐洲等地的種子都在他手中流轉,就這麼到了90年代。
九七年主權移交前後,內地的改革開放推升農業自給能力,海外供應商可直駐,謝天佑感到「香港做中間人這個位置開始邊緣化」。農產品源源不絕供港,香港過去「四處舶來」的中介角色逐漸失去優勢,他明白「若公司要在下一個紀元生存下去,2000年是一個大步。沒有自己的產品,只靠貿易,一定被邊緣化。」是時候求變。
千禧年後研究育種 邊學邊做
「事業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談起自2000年以來轉戰育種研究的歷程,謝天佑幾次提起這句話,語氣裏沒有豪情,只有一種長期作戰的平靜。
回憶初轉育種研發時的社會氣氛,他特別提及當時香港剛推行創新政策,時任特首董建華提出從「人力密集型」經濟轉為「智慧型」經濟,設立基金鼓勵科研。「不去創新,你怎麼製造財富呢?但社會普遍想法傾向找快錢,我就想去研發自己的產品。加上我也是科班出身,純粹坐着做買賣是不願意的。」
現實並不浪漫。從貿易轉為自發研究種子改良,幾乎等於從零開始——沒有政府補助,沒有育種專才,連研發架構都得邊學邊搭。2000年前後經濟不景,失業率高企,他請來一批大學畢業生,「很多人沒有農業或育種背景,我就派他們去台灣的「亞洲蔬菜研究發展中心」(今「亞蔬-世界蔬菜中心」)受訓」。高華從那時開始,逐步建立起自己的育種團隊與研發格局。「一開始什麼都沒有,走到今天都還沒看到路的盡頭。」謝再補了一句。10年,又10年。育種不是一年半載就能組出「爆款」的產業,從選育到穩定上市,以10年為計也未必能成就足夠成熟、被市場廣泛採用的成果。
在香港雖能繁育華南一帶的品種,但若要長期做種子研究,仍得向外走,「生產蔬菜和生產種子是兩回事」。謝天佑解釋,育種就像在原料池裏尋寶,要從地方品種中找出具潛力的性質或風味,再進一步改良。「以今天高度商業化的生產來看,華南地區的地方品種在產量、抗病、適應性等方面仍有欠缺,所以我們種子公司就有機會去改良它,轉移到第二地再改良、迭代。」由於華南地帶濕熱多雨、梅雨季漫長,高華便將部分育種工作轉移到氣候更穩定的地區。高華陸續在廣東開平、昆明、台灣與泰國設點,將育種研究的環節放在最適合的氣候帶,像是把有潛力的孩子送去更適合鍛煉成長的地方。「20年,我都沒有什麼好的產品出來。」他不諱言,「高華的工作可以說是仍未成功的,20年對育種來說,還是一個很短的時間」。雖然這句話以「賣得到錢」、「改變供應結構」作為標準,但高華的研發路徑與着手的品種也在這段時間走出了自己的方向。
在地品種欠備份 風味難再現
地方品種為何要保育?地方品種,是一地民間智慧與環境互動長年沉澱的結果;它們常在風味、耐性與適應性上各擅勝場,但在產量、抗病層面參差不齊,未必能直接規模化商用。作為民間企業,高華的資源有限,只能針對特定品種、面向當下的農業市場調整。謝天佑也強調另一條脈絡:「保育香港本地品種是一個問題來的,那不是一個商業上可以維持的工作。那些工作我們暫時沒有能力去做,雖然很重要。」這條脈絡需要研究機構與公共種子庫去承擔——由研究機構把地方品種收進基因庫,為將來氣候變遷下的新病害與新環境留住可用基因。「如今本地已數十年無人種稻,要研究,種子從哪裏來?」他以香港稻為例:「幸好上世紀50、60年代政府曾把樣本送往美國基因庫,後來中大才得以申請回來;沒有備份,就等於永久消失。」
2012年前後,高華曾參與復育粉嶺鶴藪村的本地白菜「鶴藪白」。「這是香港一個原生品種,真的特別好吃,但市面上(現有的產品),個個都認為那不是(原先傳述的風味),我們就想要弄一個出來」,謝天佑回憶。這道題的難處不在「能不能種」,而在「怎樣的風味才算對」:早年對在地品種的形態與風味缺乏標準化文字紀錄,亦無種子庫備份樣本,村民與菜販只會說「不似從前」,卻難以具體描述差異。團隊經過復育工作,最後採取以「口述記憶」判定,請在地耆老現場指認,再把外觀與風味最接近記憶的一型留種。這個案子不以商業為目的,但算作保留地方記憶與風味的一種嘗試。
若從基因譜系與風味記憶出發,香港的菜從來不是一個封閉的概念。謝天佑亦解釋:「新界以前投入種菜的多是大陸來的移民,種菜是很辛苦的工作,本地少有人做這些辛苦的農務,早期以種水稻為主。」長期從事農業的多由潮州、增城等廣東地區遷移而來,他們帶來粵東一帶的栽培經驗與品種,在不同的土壤與氣候條件下慢慢變異,也隨時間滲入今日的在地記憶之中。「比如常見的荷塘芥蘭,就是廣東有個村鎮叫做荷塘,因此得名。」謝天佑補充道。
追根究柢,若執著於「何謂原生」則剪不斷、理還亂。與其強行劃界,不如將「重視地方品種」看作對風味與記憶的珍惜。種子好比流動中的錨,落地之處,便生出一代代人與空間的互動,留下特定的味覺感受與家常菜譜口訣。
不執著原生土壤 須考慮地理氣候
自謝天佑回港的70年代至今,香港人工與地租早已翻了數倍,單靠賣菜與種子,公司難以應付農業研發與生產所需的各項成本。大量農地在基建與房地產發展下被轉用,農業的生產與市場空間不斷被擠壓。他回憶,英治時期內地尚未向港大批供應蔬菜,那時人們對土地的想像仍是「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如今則必須更精細地思考「因地制宜」,甚至「因緣移地」。
對種子研究而言,關鍵不在「是否留港生產」,而在把研發與生產放置到最合適的地區。現今,南港島已不復見昔日的田畦,高華花園多數自耕地已停耕,成為公司的主力辦公空間,餘兩座溫室作為育苗園地,也與本地農商有所互動。主要育種工作轉移至新界與內地,市場重心也早已越過邊界。高華的轉變和育種思路,像蒲公英從一株散成多株,離開原生土壤與舊市場,卻在新的空間裏尋得延續的可能。
謝天佑觀察到,年輕人對農業確實關懷,「但多數停留在理想與體驗」。他認為現階段高華沒有宏大的計劃,在香港做農業與農學相關的研究,最大的障礙仍是人手與成本;然而,他並未失去耐心,香港已不再是單一的生產場,而是區域農業體系中的一個節點。「即是,我設計了一個產品,在哪裏製造不一定要黏在一起,我在哪裏做不要緊。」在更遠的地方,那些延伸出去的品種仍在田間生長。
文˙ 于惟嶼
{ 圖 } 曾憲宗
{ 美術 } 張欲琪
{ 編輯 } 王翠麗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