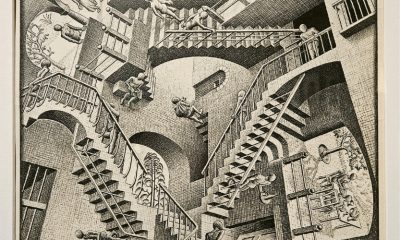副刊
【倫敦】公關災難以外:蔡國強《升龍》短評

【明報專訊】本來今個月是想要寫V&A East Storehouse最新開幕的David Bowie Centre的,畢竟我的一個好朋友有份參與那個計劃,正好可以再來一篇專訪。然而計劃趕不上變化,一來,我搶不到票;二來,上星期我看Instagram、Threads的時候幾乎被「始祖鳥」、「藝術家蔡國強」、「炸山」這幾個關鍵詞淹沒了。正好,我一直都想說一些與戶外藝術有關的話題,所以今期與倫敦的文化藝術無關,純粹是我自己對於蔡國強的藝術煙花項目《升龍》的一些看法。
就這個事件,由於環境污染、生態保育這些論點已經被無數KOL、媒體反覆挖掘過了,因此我不打算在這裏再重複一遍。畢竟我不是環保鬥士,而且從這個語境出發的話,討論的都不外乎是「誰批准的?」、「還有多少殘留化學物?」、「誰來補救?」之類的問題,感覺這些批判都有點同質。反而關於作品本身的評論是少之又少,看了不少網民的評價,我最常見到的是說這個作品「醜」,然後就沒有了。真的是那麼簡單直白嗎?就算不喜歡一個作品,應該也要嘗試一下分析箇中原因吧?
戶外藝術,無論是在城市中心,還是在自然環境進行,對於藝術家來說都是一個挑戰。原因是,一旦藝術品沒有畫廊這個把藝術品與外界隔絕的空間,發揮類似畫框的作用,那麼作品就必須要與展出的場域展現某種關聯或對比才得以成立。就以藝術家Christo and Jeanne-Claude的作品The Floating Piers和Wall of Oil Barrels – The Iron Curtain為例,這兩個作品的核心概念都是利用物件或物料來改變藝術品展出場域的面貌甚至是地貌,讓觀眾以一個新的方式或視點來感受該場域。因此作品就好像是與空間對話一般。在這個語境底下,作品、藝術家、場地是處於對等的狀態,三者都需要為對方調整。以上這些作品不是沒有環保方面的爭議,但是為什麼它們被認為是優秀的戶外藝術,而《升龍》則備受批評?
《升龍》這個作品,用蔡國強的原話,確是有「大鬧天宮」的感覺。它在創作過程中,牧民牲畜需要被遷移,野生動物也要被引導離開燃放區。在這些前提下,再破壞地貌,就有點「霸王硬上弓」的觀感。在作品中我沒有感受到對自然的尊重,反而只有人的傲慢,以及自我膨脹。用這些方法創作,這個作品基本上在任何地方都能完美重現。那麼,為什麼必須要在喜馬拉雅山進行?黃山不行嗎?鳳凰山不行嗎?這種源於自大的割裂感,大概是我對這個作品最大的感受。
其實我很喜歡蔡國強早期那些利用爆破來探討書法和繪畫為何物的作品。那些作品利用爆破的不可控性,來對書法和繪畫這些創作方式發出的提問是很前衛的。而他近年的作品,卻變成了那種「老練的花火師用自身的經驗來創作自己腦海中的畫面」的類型。作品變得更美輪美奐,更易入口,但是以前那種曖昧性則消散了,有點可惜。
文:Michael Cheung(當代藝術家,現居倫敦,畢業於 Central Saint Martins。個人網頁:michael-cheung.com)
[開眼 大都會文藝誌]
日報新聞-相關報道:
【大阪】《棋魂》原畫展:千年的感動 (2025-10-03)
【紐約】我織我所見:阿富汗戰爭毛氈 (2025-10-03)
【香港】熒幕—展覽 (2025-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