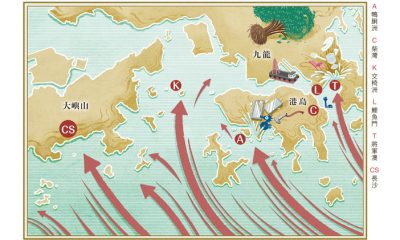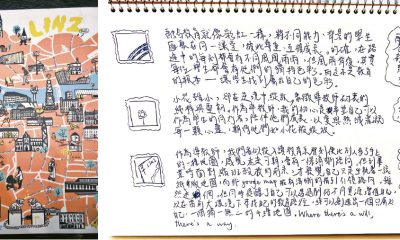副刊
A to Z藝術字典:O-Oil Paint油彩

【明報專訊】當我們走進博物館或美術館欣賞畫作時,觀眾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作品的內容、技術和畫家的名氣上。「究竟那張畫畫什麼?色彩構圖是否吸引?畫得好不好?畫家是誰?」除了這些元素,我們也許甚少留意作品所使用的媒材(Medium)及它的特點,也甚少提及它的故事,今期想跟大家談談「油彩」(Oil paint),這種在古典畫(Classical painting)經常使用的媒材。
油彩的歷史
油彩(或譯作:油畫顏料)自文藝復興時期就深受藝術家喜愛,至今仍被廣泛使用。它不僅色彩飽滿、質感豐富,還具備極高的可塑性與持久度。相比水彩(Watercolour)或塑膠彩(Acrylic paint),油彩的乾燥時間較長,讓畫家有充分的時間雕琢細節、混色及慢慢疊加層次,營造出細膩甚至高度像真的效果。如林布蘭筆下充滿戲劇張力的畫面、梵高以厚重筆觸描繪的星空,以至盧西安.佛洛伊德(Lucian Freud)那淡然疏離的人物肖像,皆展現出油彩在質感與情感表達的多樣性。
在油彩出現之前
當我們談及油彩的歷史,不得不追溯至中世紀晚期到文藝復興初期。雖然早在公元7世紀前已有用植物油調和顏料,但真正將油彩技術發展成熟,並廣泛應用於藝術創作的,則要數15世紀初活躍於法蘭德斯(Flanders,今比利時地區)的畫家揚‧范艾克(Jan van Eyck,約1390-1441)。
他早期常被誤以為是油彩發明者,實際上他是一位革新者。揚‧范艾克改良了顏料配方,並運用透明罩染技法創造出前所未有的光澤感與豐富層次,大力提升了油彩的表現力,使畫面更具真實質感。他的代表作《阿爾諾非尼夫婦像》(The Arnolfini Portrait,1434),其細緻度及描繪能力實為人驚歎,成為藝術史上重要的作品之一。這重大的改良技術,使油彩成為20世紀塑膠彩發明前的主流媒材。
「蛋彩」的限制
在油彩普及之前,歐洲畫家一般使用「蛋彩」(Tempera),這種技法早在古埃及、拜占庭與中世紀歐洲被廣泛使用,常見於木板畫。蛋彩以蛋黃作為黏合劑,混合天然色料使用。其特點是乾燥速度非常快,因此畫家必須迅速作畫,無法進行太多修改。儘管色彩鮮艷,但表現力較為平面。
油彩的出現為畫家帶來更大的創作自由,加上畫布逐漸取代木板,成為最常見的底材。無論是顏料的表現力或畫面尺寸,均為當時的藝術家帶來前所未有的繪畫體驗。油彩從北歐傳至南歐,迅速風靡整個歐洲藝術界,深深影響西方藝術的發展軌迹。
達芬奇的實驗
說到油彩的歷史與發展,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的經典之作《最後的晚餐》(The Last Supper)無疑是不可忽視的重要案例,也是一段關於媒材實驗的冒險故事。《最後的晚餐》創作於1495至1498年間,位於意大利米蘭聖瑪利亞感恩修道院(Santa Maria delle Grazie)食堂牆上。由於傳統的濕壁畫技法(fresco)必須在濕灰泥上迅速作畫,難於處理畫面細節,熱中技術創新的達文西決定放棄這種傳統畫法,嘗試在乾燥牆面上結合蛋彩、油彩與其他黏合劑這種充滿實驗性的方式作畫。這項實驗最終在技術層面上並未成功。由於油性材料無法穩定附着乾燥牆面,加上牆後廚房長期釋放的濕熱蒸氣影響,畫作在完成後短短數十年便開始變色剝落,畫面逐漸受損。現今我們看到的版本,其實是歷經多次修復,方能挽回部分原貌。究竟原作效果如何,或者只有當時的觀眾才知曉。
什麼是油彩?
油彩是一種將色料(pigments)與乾性油(drying oil,如亞麻籽油、罌粟油或核桃油)混合而成的繪畫媒材。這些乾性油能與空氣中的氧氣發生氧化作用,慢慢固化成堅固且防水的薄膜,將色彩牢牢固定在畫布或畫板上。
在現代支裝顏料(tube colour)出現之前,畫家必須親自調製所需的油彩。顏料主要以乾燥的色粉形式存在,即「色料」,其來源包括天然礦物、植物、動物萃取物,以及人工合成的色料(synthetic pigments)。這些色料本身不具黏性,無法直接附着於畫布,必須與乾性油充分混合,才能製成可供繪畫使用的油彩。整個過程不僅耗時,亦講求技術與經驗,因為顏料的品質與配方會直接影響畫面的色彩表現與保存狀况。色料的穩定度並不盡相同,有些色彩隨時間推移會逐漸褪色或變質,尤其在光照、濕度等外在條件影響下,畫面的原貌可能難以長久保持。因此,畫家在選用色料時,除了追求色彩效果,也必須考慮其持久度。
不同色料具有獨特的色澤、透明度與耐光度,例如來自青金石(Lapis lazuli)的群青藍(Ultramarine blue)、由紅蟲(Cochineal insect)提煉的胭脂紅(Carmine red),以及含鉛的鉛白(Lead white)等,皆為歷史上廣泛使用的重要色料。由於原料來源的稀有程度不同,色料之間的價值亦高低不一,畫家會根據創作需求與可得資源,謹慎挑選與調配顏料,以展現畫面內容與個人風格。
比黃金還珍貴的群青藍
你或許聽過,群青藍曾是最昂貴的色料之一,甚至比黃金還珍貴。它來自稀有礦石青金石,主要產於阿富汗的巴達赫尚山脈。為了提煉這種色澤純淨、深邃鮮明的藍色,需將礦石反覆研磨、洗滌與分離,工序繁複,成本極高。在中世紀與文藝復興時期,群青藍必須經由絲綢之路等漫長的貿易路線運抵歐洲,進一步提升其價值。畫家通常只會將其用於畫面中最重要的位置,特別是宗教畫中聖母瑪利亞的長袍,以象徵神聖與純潔。由英格蘭國王理查二世(King Richard II)委託繪製的《威爾頓雙聯畫》(The Wilton Diptych,約1395-1399)正是代表性作品之一,畫中大量使用群青藍,不僅突顯畫面主體,也彰顯皇家委託作品的尊貴地位。
普魯士藍 第一種人工製藍色
天然群青藍價格高昂,這促使科學家努力研發更經濟的替代品。18世紀初,德國化學家約翰‧雅各布‧迪斯巴赫(Johann Jacob Diesbach,約1670-1740)約於1706年在一之意外中首次成功合成「普魯士藍」(Prussian blue),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種人工製造的藍色顏料。隨着工業革命出現,科學技術與化學工業快速發展,普魯士藍得以批量製作,成本大幅降低。相比天然群青藍,普魯士藍色澤鮮明,耐光耐久,更最重要是價格低廉,因而在歐洲藝術界迅速普及,成為不少畫家喜愛的顏料之一。
這種新顏料不僅在歐洲廣受歡迎,也經由荷蘭貿易傳入亞洲。普魯士藍於1747年透過長崎進入日本,後來在江戶時期(特別是1820年代以後)於浮世繪中被廣泛使用,稱為「ベロ藍」(Beroran),這正是普魯士藍的日文譯音。它逐漸取代過去常用的植物與礦物天然染料,這些傳統染料色澤較為淡雅,且不易保存。相比之下,普魯士藍色彩鮮明穩定,令畫作更為生動,開啟了浮世繪色彩技術的新篇章。日本著名浮世繪大師葛飾北齋(Katsushika Hokusai,1760-1849)的經典作品《神奈川冲浪裏》(The Great Wave off Kanagawa,約1831),就是用了普魯士藍。有趣的是,這些日本畫後來又傳入歐洲,甚至對印象派畫家產生了深遠影響,成為藝術史上一段橫越地域的文化交流。
現代科學鑑定與顏料
顏料的作用並不止於藝術創作的層面,隨着現代化學、物理學與顯微技術的進步,它亦是判斷作品真偽的重要線索。現今透過「科學鑑定」,專家可分析畫作中所使用的色料,判斷其是否符合該時代的媒材特徵。例如,若一幅標示為17世紀的畫作中出現了19世紀才有的鉻黃(Chrome yellow,梵高常用的黃色),或20世紀才合成的鈷藍(Cobalt blue,莫內《睡蓮》的藍色),那意味這幅畫極可能是後人偽造。這類技術曾揭發多宗著名的偽畫案例,其中包括匈牙利出生的猶太畫家艾米爾‧德‧霍里(Elmyr de Hory,1906-1976)與荷蘭畫家漢斯‧凡‧梅格倫(Han van Meegeren,1889-1947)兩名聞名於世的偽畫家。他們雖能巧妙模仿各大名畫的畫風與筆觸,早期曾瞞騙不少人,但即使畫風如何逼真,最後卻因顏料成分與時代不符,露出重大破綻。
大家下次看展覽時,不妨留意畫作旁邊的「作品標籤」(Caption card), 嘗試留意一下作品所用的媒材與作品之間的關係,或許會有更多有趣的發現!
文˙ 葉曉燕
{ 圖 } 網上圖片
{ 美術 } 張欲琪
{ 編輯 } 王翠麗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