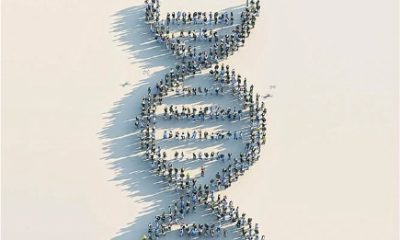副刊
通識導賞:尋找自身文化的東方卡巴萊 最終還是Be yourself

【明報專訊】如果「有歌聽、有嘢飲」也可以是卡巴萊(Cabaret),在我們的土壤裏,其實有沒有這種文化?卡巴萊是舶來品,登陸東方前,若探究其形式,中國的茶館作為社交聯誼的場所,再加上相聲、歌女演唱等節目,是否也是卡巴萊?在劇場、音樂劇傳到亞洲以前,那些歌廳、夜總會,燈紅酒綠的世界裏,多少是自家傳統,多少是受外來影響?經歷殖民時代的亞洲城市,自然會發展出一套夾雜西方與傳統的獨特文化。當然,卡巴萊不單只是形式。半過世紀以來,亞洲如何移植西方,再發展出屬於自己的一套卡巴萊?
【系列二之二】
日韓:夜場走進劇場
誕生於19世紀的卡巴萊跟其他西方文化一樣,隨着戰火、殖民傳入亞洲。一般來說,早期都是歌廳模式,像韓國經歷日治時期與韓戰美軍駐紮的年代,首爾及港口城市興起了夜總會、舞廳,後來又有美軍俱樂部,歌手演唱、現場樂隊,甚至脫衣舞及雜技等,皆有卡巴萊的特質。而在台灣,隨着國民政府在1949年遷移台灣後,也帶來十里洋場的上海文化。1960年代的西門町出現很多「紅包場」,因觀眾會將現金放入紅包中,直接打賞給歌手而得名。紅包場其實是模仿上海的歌廳, 穿上旗袍的歌手演唱上世紀20至50年代的老上海歌曲,觀眾多為退伍軍人,高峰期,西門町有10多家紅包場。隨着時代變遷,許多場所關閉。紅包場不僅是娛樂,亦反映了戰後移民的鄉愁。
跟歐美一樣,卡巴萊在亞洲也逐漸演變成主流娛樂、旅遊景點,好像日本的卡巴萊文化差不多等同是夜生活。東京六本木的「Rokusan Angel」(前身為Burlesque TOKYO)一般被形容為日本版的紅磨坊,結合歌舞雜耍、鋼管舞,有性感舞孃,又有kawaii偶像裝扮,更會邀請觀眾上台,雖然是「20禁」,卻是男女皆宜。而另一家「六本木金魚」則以現代的「歌舞伎」為概念,融合傳統與創新的舞蹈,而表演者中有男性、女性、男扮女裝或變性舞者。這兩個場地都是以夜總會為基礎。而在淺草的Kaguwa劇院,則結合傳統日本文化和當代音樂。表演者穿上和服,在現代舞蹈、戲劇中融入日本傳統的獅子舞、武士武打場面和藝伎的元素。日式的卡巴萊以遊客為目標, 一般都要預約,提供餐飲服務,嚴禁拍攝。舞蹈是重要元素,特點是加入日本的傳統文化。而韓國方面,隨着創意產業興盛,音樂劇的流行,卡巴萊逐漸進入專業劇場,像首爾「House of Tease」、「Seoul School of Burlesque」,專注培訓和製作,為商業項目製作卡巴萊形式的演出,不少音樂劇亦已融合卡巴萊元素。
台灣:從「歌廳秀」到文化傳承
近年台灣的劇場也發展出一套台式的卡巴萊,承傳自昔日「紅包場」的形式。瘋戲樂工作室自2014年起推出卡巴萊系列,以英文金曲、華語流行歌、耳熟能詳的歌曲、劇場,拼湊出像是「百老匯」和「紅包場」的混合體。其創辦人、藝術總監王文希指台灣的「歌廳秀」文化也是跟卡巴萊百老匯類似的東西,只是今天觀眾想到歌廳,以為都是低俗或是情色的面向,而忽略了這種融合歌舞、喜劇、脫口秀或相聲的小劇場,其實是最親民的。他認為看表演不一定要那麼嚴肅,可以是很有互動的,「請放鬆點吧,想鼓掌就鼓掌,想大叫就大叫!」
從自身文化中抽取養分的,還有近年躍於台灣各大音樂節的金秋大樂隊,以爵士大樂團編制,編曲重新詮釋國台語、西洋經典或流行歌曲炮製的一種「台味爵士」。2025年在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上演的《金秋歌廳秀》,以帶有拉丁或是日本風格的閩南語金曲、傳統與現代爵士,改編為大樂隊演奏版本。這種以創新手法重現當年閩南語黃金時期的時代,也是一種文化傳承。而在劇場裏,2023年在衛武營上演「【衛武營小時光】唱歌集《愛(AI)妻》Cabaret」,也就是改編自韓國2019大邱國際音樂劇節「最佳原創音樂劇」《愛(AI)妻》。大劇場以外,也有回到最初,在非正式表演場地的小型卡巴萊。「柳隅茶舍×卡巴萊之夜Cabaret of Taiwan」,就在「柳隅茶舍」的空間演出,並公開報名招募表演,當中有這樣的介紹:「這是一個不屬於誰,沒有賺錢可能,(不)期望有成名機會的表演練功場,請看官放心,卡巴萊唯一的要求就是要視同正式演出,你會看到很多的實驗、嘗試。」
香港:懷舊酒廊文化興起
香港在70年代流行的娛樂場所如夜總會、酒廊,也有歌手登台獻唱,而在電影電視中,這些酒廊歌手,很多時是失意的人,台下觀眾冷淡,只顧飲酒猜拳。不過現實中,那個年代活躍的酒廊歌手,其實很受歡迎兼掙大錢。他們唱的是別人的歌,與觀眾打成一片,是非常地道的香港文化。那邊廂,酒店裏的高級歌廳,例如文華酒店Harbour Room也有卡巴萊演出,70年代曾邀請Eartha Kitt等國際紅星登場。80年代,中環藝穗會的出現,「奶庫」(Fringe Dairy)亦成為早期的爵士卡巴萊式劇場代表。
舊時代過去,迎來的是懷舊潮流。近年在中環開業的中環酒吧Maggie Choo’s HK,以卡巴萊為概念設計了一個故事:虛構人物Maggie Choo在戰火之下,失去了家人成為孤兒,繼承了家族古董店之際,發現店內有一道隱藏的門,門後是東印度貿易公司所興建、荒廢了的銀行,於是將其改造成一所高雅的秘密場所。卡巴萊不止是形式,也是節目主題,酒吧以懷舊夜總會模式,將20年代上海與香港文化交融,舞蹈、爵士樂、藍調,還設有DJ。東西交匯,結合了殖民歷史與當代香港元素。
跨地域跨語言 港式卡巴萊多元探索
至於劇場裏的卡巴萊,似乎是近年的新嘗試。2019年,伍宇烈與音樂人盧宜均及劉榮豐創作的《Tri家仔》,以歌廳形式,唱出香港人特有的語言特色。從英文、中英夾雜到今天的兩文三語,「食字玩字」,以跨語言文化的特色和幽默,探索香港人的文化身分;2023年參加新加坡濱海藝術中心的華藝節,被形容是「一場獨特的三語港式歌舞秀」。
至於2025年的「西九夜延場」Cabaret之夜,進一步探索港式卡巴萊的可能。利用戲曲中心的茶館劇場,每月兩三次的相聚,晚飯後,喝一杯,近距離欣賞表演。小小的舞台,有似曾相識的名字,平日在不同媒介也看到其身影,也有新鮮的名字。在這裏,他們不是哪個作品的演員、舞者,不再演別人的故事,唱別人的歌,而是作為創作者,用最擅長的方法分享個人故事、創作與藝術之路。就像佘樂妍用交友apps與個人創作歌曲,一人的劇場說說男男女女的相遇;音樂劇演員黃溥然用喜愛的香水說故事,氣味、情緒編織音樂小劇場;張雅麗以自己的歌,訴說人生經歷,結合劇場與戲劇治療。這個舞台,同時也找到來自世界各地,在香港生活多年的音樂人藝術家,像來自多明尼加的音樂人Chris Polanco陳杰,來港工作25年,從主題公園工作到流行歌手的合作,他的卡巴萊是夾雜西班牙文、英文、粵語、國語歌曲的成長及音樂旅程。也有像置身爵士酒吧,摸着酒杯底,聽聽移居香港的南非爵士歌手Talie Monin的音樂選擇。
台上台下be yourself
一個鍵盤一支結他、小樂隊、小劇場、獨腳戲、結合影像元素、純粹的音樂,小型音樂劇的特色。音樂類型多元,流行曲、爵士、hip hop、a cappella,在這個平台上,有最地道的廣東話,也有夾雜廣東話、普通話和英文,呈現香港的多元文化,也是年輕藝術家的試練場。台上台下幽默、輕鬆愉快的氣氛,也是觀眾忘憂放鬆的地方。來自歐美的卡巴萊,總帶點情色、諷刺的味道,「flamboyant」是其關鍵詞,背後是探索自由的一種精神。來到東方,土壤不同,脫下艷女郎的形象,放下尖銳的刺刀;有時少了艷光多了含蓄,卻依然幽默,也繼續是形式多變。亞洲的卡巴萊,抽取其形式,展示自家城市的文化,像日本結合了傳統和服、武士和藝伎文化,台灣的老歌,香港的語言特性、國際性,最終都是探索文化身分的一個旅程。
巴黎歷史悠久的卡巴萊Madame Arthur主角Romain Brau如是說,「We need to laugh today, but the fight must go on—nothing is certain. Cabaret is an art where everything can be said, where you can be anything」。
不論東西方,卡巴萊的核心價值,就是分享故事,與觀眾交流。表演者可盡情展現自我,觀眾開懷歡笑。台上台下,be yourself。
文˙ 林喜兒
{ 圖 } 作者提供
{ 美術 } 張欲琪
{ 編輯 } 王翠麗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