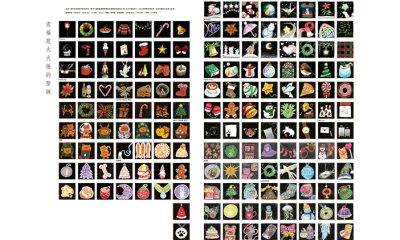副刊
有書緣:大歷史與小人物——《長安的荔枝》中的玩笑與認真

【明報專訊】近來電影《長安的荔枝》上畫,我因為喜歡原著小說的作者馬伯庸,所以很快就進戲院看了。
我從小喜歡看各種「雜書」。我是在90年代中期考中學會考的。那時是十五、六歲的年紀,家居狹小沒有自己的書桌,我就常常躺在牀上,大腿擱着課本,努力地向父母家人表演用功溫習。但實際上,課本內夾着的是各式各樣的幻想世界:厚厚的《西遊記》和《三國演義》固然是宅男恩物。另外,金庸古龍的武俠小說、田中芳樹的架空歷史小說等等。只要是有趣的,我都會翻來覆去看,看得爛熟。
現在人到中年,看這些「雜書」的興致半點不減,但口味可能變得更偏了。
我現在會找這些作品的二次創作來看。因為已經爛熟,所以對當中的人物設定和情節等等都瞭如指掌,在二次創作中想看到的就是以忠於原著風格來創作新故事,又在不破壞舊有人物和情節設定的限制中找到異想天開的新組合。因此,我遇上了馬伯庸。
風格:玩笑、小人物、具體細節
我初接觸馬伯庸時,他已有鬼才之稱。因為他的作品往往是戲仿一些我喜歡的小說,所以馬上吸引到我。譬如我很喜歡的《銀河英雄傳說》,他就曾模仿田中芳樹的獨特文風來寫了續篇。他也延伸《西遊記》,寫成《西遊樂記》,將唐僧一行人變換為四人搖滾樂隊。《湘西航班》則是將小時候看的殭屍先生式的故事轉移到了以客機遠距離趕屍的古怪場景。於是,我看他的作品時,很有在90年代共同成長的同代人共鳴,有時會因為他一本正經地將舊故事撞入新元素而邊看邊傻笑。
但馬伯庸的玩笑不只是有趣。他的作品既結合現在稱之為「腦洞大開」的新角度,也有對小人物的關懷同情,與及在傳統大歷史論述下往往忽略了的具體細節。他會由小人物的角度作歷史翻案,譬如《三國配角演義》說了很多有關街亭之戰、宛城之戰和劉禪另一位兄長等等有趣的另類陰謀論想像;《長安十二時辰》就更有趣,將美劇《24》要在24小時之內完成破解反恐任務的緊湊結構,套在盛唐長安,描寫落魄「警官」要在十二時辰內制止針對上元節花燈大會的恐怖襲擊。
另外,他也寫了一些有關歷史細節的考究,特別着重古代的數據收集和統計。《長安十二時辰》就有很誇張的大數據分析。另外,他在散文《不該小透明的曾鞏》中,仔細回顧了唐宋散文八大家中最沒有人留意的曾鞏,發現他擅長政務和規劃分析,地方治理能力很強,文如其人地既扎實又務實。《怎樣讓大明變得透明》甚至是學術形式的歷史論文。他分析戶籍制度,說古代早已以數據掌握人口與資源,讓全國變得透明,並以此有效率地運轉國家機器來動員人力物力。這套數據系統始於戰國時秦國變法,並被蕭何承傳到漢代,然後或斷或續地延續到明代的戶籍制度。
《長安的荔枝》的三重矛盾
《長安的荔枝》揉合了以上3點來重新演繹「一騎紅塵妃子笑」——唐玄宗為楊貴妃送上鮮荔枝的歷史故事。作者的惡搞可能比較收歛,但有心的讀者仍然可以留意得到。「做人最緊要開心」是馬伯庸對香港電視文化開的一個玩笑。小說中嶺南的不同人物都曾對認真又心急的男主角李善德說過,令已經焦燥的他哭笑不得。另外,李善德的好友,除了電影中的杜甫杜少陵外,小說中其實還有韓承。但這個韓承是誰呢?小說看到一半有點好奇,上網卻找不到。臨近結局時,馬伯庸以一語成讖的方式來揭曉他原來就是杜甫在安史之亂後送別的韓十四。
不過《長安的荔枝》的重點更多是放在小人物與數據收集分析上。主角李善德的設定正正是馬伯庸最喜歡留意的那些隱於大歷史下的小人物。他是負責具體安排的底層策劃人,「不懂官場之術,不諳修辭之道」,「一生熟悉的只有數字,也只信任數字」。他最後以實驗方式結合excel表格,千辛萬苦地找出每一個環節都細細相扣,短時間內運送新鮮荔枝的最佳路線與方法:「從驛站之調度、運具之配置、載重與里程之換算、乃至每一枚荔枝到長安的腳費核算」,他都無不仔細安排。馬伯庸在後記中也寫到李善德的原型,原來是來自翻查明代材料時,留意到的一位在物資調度過程中勞累至病死的基層小吏。
像李善德這樣一個理性謹慎、思慮周密的人,被作者置於唐代皇權鼎盛、天寶年間最繁華的一刻,於運送荔枝的過程中陷入環環相扣的三重矛盾之中:人與非人、體制內與超體制,和落實人與話事人。
小說中會幫助他的,除了遠在長安的兩位好友,就只有那些「體制」以外,非我族類的「非人/不是人」,包括波斯胡商、荔枝園的峒人阿僮姑娘,以及林邑奴。特別是後兩者,日常生活中自覺被唐代社會當成是一條跑到榻上的「細犬」和「一隻會講話的賤獸」。當他們被視為人而獲尊重時,就會傾全力以報。李善德也感同身受,因為自己作為基層小吏,於長安20多年,「如老犬疲騾,汲汲營營」,也想要得到身為一個人的尊嚴。但運送荔枝的過程,卻無法回報甚至有負於這些曾幫助他的非人,因此內心愧疚。
這就牽涉到體制內與超體制的矛盾。在體制內的「人」,幾乎都是與他作對的,因為運送荔枝對他們而言無利可圖,甚至李善德的成功有可能被視為他們無能的證據。於是體制內的人群起反對,直至這兩點改變:1. 李善德明白到體制內利益均霑的道理;2. 右相楊國忠倚靠唐玄宗的權力與愛惡,以令牌來超越體制流程,將整個大唐的各個環節和人力物力資源充分地動員起來而全速運轉。
體制成立後會變得因循,如果不是以超體制力量直接加以干涉,根本無法以動員。但如果落實人盡心竭力地籌謀,又以超體制方式充分運轉大唐的國家力量,可惜話事人指向的方向只為唐玄宗的私心與楊國忠的貪瀆呢?故事的結尾就以李善德對楊國忠的質問作結,也由此而直指安史之亂的根源。這就是電影海報上宣傳的社畜求生故事的另一面了。
文˙曾仲堅
編輯˙梁曉菲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