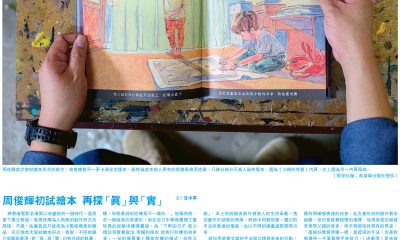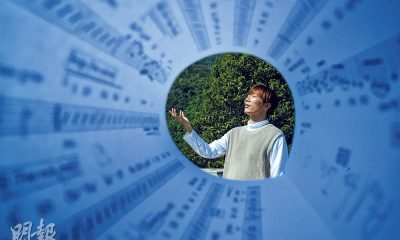副刊
「創作營」為年輕導演鋪路 電影夢從短片開始

【明報專訊】可不可以說,我們正活在一個人人都能「拍電影」的年代?手機、相機、攝影機;電影、劇集、短視頻,工具千變萬化,媒介豐富多樣,創作變得更容易……嗎?資深監製莊澄、導演關錦鵬、電影製片人謝萌都說,似乎不是。
技術門檻或許降低,但創作的門檻從未降低。這邊廂,連資深導演也苦惱「無得開機」;那邊廂,年輕電影創作者愈發感到艱難——如何講好一個故事?又如何令故事躍上銀幕,走到觀眾面前?「國際電影創作營2025」希望為年輕創作者提供答案。
由亞洲電影大獎學院主辦的「國際電影創作營2025」(2025 International Film Camp,後稱「創作營」)剛在澳門結束。18名來自亞洲各地的創作者聚在一起「上堂」,從劇本創作、資金籌措,到影片發行與後期製作,來自電影業不同崗位的導師傾囊相授。
「我們入行那時,如果有這些創作營,一定好想參加。」莊澄感慨。曾監製《頭文字D》、《無間道》、《九龍城寨之圍城》等多部港產片的他,獲亞洲電影大獎學院邀請,在是次創作營中擔任首席導師。縱橫電影業40年,莊澄仍記得初入行時的窘迫,「沒有人問你會不會,沒有人教你,你只能慢慢摸索」,「大家都預計你全部都識,你做編劇時,不會有勇氣對導演和監製說,其實我有東西想問」。因此,在為期5日的創作營中,他不僅擔任導師,還「同每個後生仔單獨見面,一對一傾偈,他們想問什麼都得」。
8名導演獲選 資助30萬元拍短片
莊澄說,18名「後生仔」從超過380名報名者中選出,每個人都需以「我的摯友」(My Best Friend)為主題提交短片提案。經過創作營的打磨與訓練,最終8名導演獲選,每人獲得30萬港元製作15至20分鐘的短片——港人熟知的鮮浪潮國際短片節,第19屆的資助是10萬元;早前停辦,近日宣布重辦的ifva獨立短片及影像媒體比賽,停辦前的一屆金獎作品獲得的獎金是2萬元,「30萬,不是小數目」,莊澄說,因此入圍者並不完全是「素人」,而是「有相關經驗、有一定基本功,甚至曾經攞過獎的從業者」;入圍作品也很多樣,「有的表達到一些電影技巧,有的有幽默感,有的比較藝術片,有些比較商業」。
儘管入圍者大多有電影製作經驗,但莊澄仍然認為,評價15至20分鐘的短片劇本,與評價他過往監製的「大片」有許多不同,「短片時間短,所以不可以有那麼多枝節,要更加準確」;但兩者仍有相似,「無論短片還是長片,都要五臟俱全,有起承轉合。香港很多導演都是拍短片後被大眾認識的,所以兩者間有很多共通點」。
曾為參與康城影展、柏林電影節等眾多電影節的電影擔任製片,並在不少電影節擔任評委的製片人謝萌表示,近年來短片已經成為創作趨勢,「在不同的短片節,投報數字每年都在增加,甚至會達到上千部」。為何會興起短片創作熱潮?謝萌解釋,短視頻文化的影響巨大,「很多視覺產品都會用短視頻表達,新一代創作者也對用短片敘述故事興趣濃郁」。同時,以內地為例,「對於短片作品的審查,相對長片而言沒有那麼嚴格和細緻」,創作者的表達更為自由。並且,近幾年有不少亞洲短片在世界各大影展斬獲獎項,「例如唐藝的鮮浪潮短片《天下烏鴉》,在康城影展獲得『最佳短片金棕櫚獎』;鄭陸心源的短片《她房間裡的雲》,獲得鹿特丹國際電影節金虎獎,甚至賣到法國」,這些短片的成功,為創作者打開新思維,「過去大家可能從來不會想到,原來拍個短片也可以拿獎,也可以去到這麼重要的電影節」。
「去地域化」成創作趨勢
是次入圍者來自香港、澳門、中國內地、韓國、越南、吉爾吉斯等不同亞洲地區,莊澄觀察到,有的人來自亞洲,卻在歐美創作與生活;也有人在一個地方生活,筆下故事卻在另一個地方發生。謝萌說,電影創作中的「去地域化」早已成為趨勢,「甚至大家已經在取消『國別電影』這一概念」。以他擔任製作人的新作品《寂靜的朋友》(Silent Friend)為例,擔任導演及編劇的Ildikó Enyedi來自匈牙利;憑電影在威尼斯影展獲獎的新演員Luna Wedler來自瑞士,說的卻是德語;導演甚至為香港觀眾熟悉的演員梁朝偉「量身訂做」角色,「導演把他寫成從香港去到德國大學的訪問學者」。《寂靜的朋友》圍繞德國植物園中的一棵古樹發生,3個年代3個故事,植物與人類默默產生精神連結。「影片在德國、匈牙利都有拍攝,甚至在香港也有一小部分拍攝,包括聲音後期,像是梁朝偉的studio錄製,也是在香港完成」。
藉「亞洲內部合作」走向國際
謝萌表示,「去地域化」在電影內容與製作方面皆有體現,從這個角度看,「創作營帶給入圍的青年創作者的體驗堪稱奢侈」,「就算你最後沒有拿到資助,但活動本身已經為你未來創作鋪下道路。參與者來自不同地區,可能你現在認識的人,就是你未來的合作者」。他補充,「亞洲內部合作」是令更多亞洲電影走向國際的好方法,「許多國際電影節仍然是西方遊戲規則,以西方選片人為核心,他們在看待某個區域的電影時,總有一些期待看到的」,謝萌舉例,「例如香港,這個選片人在生活中如何理解香港、他見到的香港故事、對香港電影的印象,都會影響他對香港作品的預期」,「他尋找的是印象中的香港味道、美學與話題」;若沒有對當地文化相對了解的人參與其中,「如果作品不符合對方預期,可能就會被認為不適合。有更多人去溝通、對話,才能令對方理解作品的獨特」。
近年在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教書的導演關錦鵬也給創作營帶來一堂「大師課」。他笑說,近年教書「好享受」,現在只有寒暑假才有空閒拍戲。關錦鵬透露,自己的新作已在計劃中,是「兩個男仔的同性感情古仔」,演員來自香港與台灣,「現在就等演員檔期了」。教書之外,他也為《但願人長久》、《人海同遊》等不少新導演作品擔任監製。新導演交出怎樣的作品會令他「收貨」?「我好在乎你拍的人物能不能引起觀眾興趣,譬如人物之間的互動、角色與角色之間的互動可以帶動好的情節。」關錦鵬說,寫好人物是他眼中「好作品」的最重要原則。他舉例近年不少港產片都「將人物寫得好好」,例如《看我今天怎麼說》、《毒舌大狀》、《破‧地獄》、《九龍城寨之圍城》,「都貼近我印象中1980年代的戲」。
「如果回望1980年代香港電影新浪潮,可以說處於黃金年代的不止是電影,香港的各行各業都興旺——然而,那個時代已經過去,回不去。」關錦鵬嘆息,過去的日子追不返,「你問我現在怎麼做回新浪潮,我會說做不到」。眼見大環境愈來愈差,「無論是經濟,還是創作上受到愈來愈多的限制」,不少朋友問他「為何不走」,他卻反問「離開香港,我還可以去哪裏」?「香港1980、1990年代帶給我們很多東西,近日它不好了,我們就走了?我是不會走的。」關錦鵬說,就算不是親自拍戲,他未來也會「做監製、策劃、教書等工作,都是和電影發生了一些關係」。
「不要幻想第一部就好成功」
對於一眾年輕創作者有哪些建議?關錦鵬直言,「不要一入行就想着拍長片」,「如果你有一個好的劇本,在資源和資金上,短片的機會會大很多」,例如香港國際電影節(HKIFF),又如今次創作營。他還提醒創作者,與自己的劇本要「有些距離」,「既遠且近,既近且遠」。他解釋,如果過分沉溺於自己的作品中,「感動到自己,不一定感動到別人」。莊澄和謝萌則提醒創作者,要找到自己的風格。「創作風格不用經營,你就是你自己,很多人的劇本和本人都會很像——創作的過程,你一定是在發現你自己。」謝萌說。莊澄則補充,香港市場「好難觸摸」,「不要幻想第一部就好成功、好得」;不如努力「了解自己、了解他人」,「先看多些、做多些——重要是將自己浸入行業中,把握每一次機會」。
文:王梓萌
設計:賴雋旼
編輯:王翠麗
[開眼 文化力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