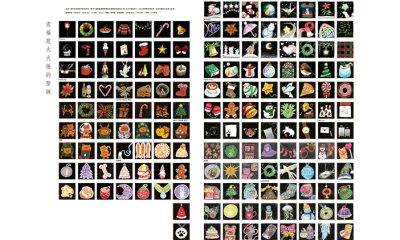副刊
{浮沉達人}周文傑 作品入圍短片「奧斯卡」 在理想與現實拉扯 繼續燃燒創作之火

【明報專訊】月頭又要交租,你看着銀行戶口又減去6000元,這是每個月唯一一筆會固定出現的交易紀錄,數數手指,再減多幾次銀行戶口就會跌破五位數。在一眼望晒、連窗也沒有的百來呎劏房,你坐在單人牀上,聽着隔壁牆鄰居隱約傳來的普通話短劇雜聲,突然恐懼自己10年後會不會仍然過着這種生活、會不會「咁就一世」。如果有一個機會,你可以搬入千呎大屋,衣食無憂,租金全免,但代價是要「證明」自己失去理智,這場交易你願意嗎?這是新晉導演周文傑在其編劇及執導的短片《歡迎入住伊「癲」園》中,向觀衆拋出的問題。短片入圍了剛過去的,美國奧斯卡金像獎認證影展HollyShorts電影節,是全球7000幾套作品中唯一脫穎而出的香港導演作品。在曾首映無數知名電影的TCL Chinese Theatre的大銀幕上,來自香港的故事得以放映。
借「伊『癲』園」展居住困境
短片第一場場景由戴玉麒飾演的主角居住的劏房開始,畫面長寬比特地縮小至一比一,有限的畫面中只放得下一張牀,映照同樣有限的現實空間——取景的劏房就是監製的朋友每天居住的家。為了通過測試,獲批進「免費入住五星級社區——最佳治療聖地」,主角每天跟着身邊的院友裝傻扮瘋,自願被24小時監視、吃不像食物的食物、跳意義不明的舞步,只為融入不理智的社區。「對於故事裏面的角色來說,他們在想,我怎樣跳或者怎樣做,你們才會覺得我瘋了呢?同時在現實生活中,我跟着大家做一樣的事,那我是不是就叫做正常呢?」這套作品的創作意念,源於周文傑有朋友為了買樓,正職以外再返兼職,同時承受經濟壓力和心理壓力,他看在眼內覺得「好黐線」,亦反思:「當你其實已經無生活可言的時候,到底這個空間對你來說還有什麼意義呢?」
在故事結尾,主角迷茫地學着狗吠,沒有主角內心獨白,管理員滿意地剔下「入住批准」。「很多朋友看完都問我,他最後是真瘋還是沒有瘋?我就說,你覺得是怎樣就是怎樣。」周文傑指導演員扮狗吠的場景時,一共拍了3個版本,真瘋、假瘋和令觀衆分不清楚真假的版本,現在採用的版本,或許連演員自己也認不出有什麼分別。「因為我覺得現實的情况就是,當我們為了一層樓那麼努力,連旅行也不去,其實你都開始分不到,到底自己是不是真的那麼想要那層樓。」周文傑用奇幻類型片,問觀衆也問自己,究竟家是什麼、你願意犧牲多少去換取理想的家、犧牲是否值得。另一個角度看,也是在問——選擇理想,而摒棄安居樂業又是否值得。雖說短片主題是居住困境,但記者一邊看,感受更深的還有年輕人在理想與安穩中拉扯的惆悵。
「我到底可以這樣生活幾耐呢?」
周文傑住在天水圍公屋,年過30歲,仍然與妹妹同住一間房間。雖然不是住劏房,居住困境於他也是切身問題,日常掙扎是應不應該放棄創作,像其他30歲的大人一樣做份朝九晚五、養得起家的工作。他畢業於香港大學,大學同學收入都比他高。和同學聚會時,大家聊天的話題是買樓要交幾多稅、九成按揭計劃,他完全插不了話。因為作為無正職、經常被拖糧、朝不保夕的人,他從來無考慮過買樓,反正自己都過不了壓力測試。「但我就見住他們一個買了這個樓盤,哪個又買了哪層樓,整個朋友圈只有我未買樓。」拍拖後,他有時也會想像10年後的生活,難道到時仍然和家人同住?「然後我都會思考,係囉,其實我有幾熱愛創作,我可以創作到什麼時候呢?」 他有一個朋友,本來都是住劏房寫劇本,後來也轉行了。「因為創作這一行,不是你一直創作就可以有所謂好的成果,或者你就會寫得好或者拍得好。但某些行業可能只要你夠努力,就會去到某個position。所以畢業後這幾年,我都會不斷問自己,我到底可以這樣生活幾耐呢?」
由記者轉跑道學電影 倒貼錢拍攝
先回頭望望創作這條路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周文傑大學時雙主修新聞學和社會學,讀書時做過港聞記者,「其實我是很享受做記者的。因為我會覺得,我報道的東西,或者我發現的東西,其實是可以影響到人。但後來發現,咦有些記者會好像老是重重複複,開始令我反思,做記者是不是真的是我最想要的東西呢? 」同時有師兄找他幫忙拍短片投稿鮮浪潮,到大四參加聯舍話劇比賽,寫一個關於無家者被趕走的故事,贏得最佳導演和最佳劇本獎。這契機令他開始想嘗試用戲劇的方式說故事,用電影影響世界。於是他畢業後再報讀香港演藝學院電影電視學院學士課程,主修導演。
由記者轉換跑道到電影創作,雖然傳媒行業也不是高薪厚職的舒服工,但在朝氣蓬勃的20出頭,再花4年時間重頭學過、又要申請Grant Loan背負學債,投入前景飄渺的電影工業,不是輕易的抉擇。「那時都有很多人質疑我,一些電影行內的人跟我說,為什麼你又浪費4年時間去讀書,你出來工作,一邊做一邊學就得啦。但那時候我又很覺得,唔係囉,我想做的是創作者,不是operater。」學院讓他學到電影理論、感受創作氛圍,到台北藝術大學交流時,老師跟他討論電影哲學,為什麼要用這個顏色、顏色代表什麼、為什麼要用close up,教他反思創作的每一個畫面。「令我發現,其實電影創作,你要對這個世界要有很多的思考和觀察,而不是純粹很工業式的製作。」
但離開美好的學院後,在現實的電影工業世界,熱情不能當飯吃。「通常導演系畢業,都是乞食的。」周文傑笑着道出演藝學院畢業生的共同命運。一是靠人脈介紹去大公司做正職,人工一來偏低,二來也要由場記、助理開始做起,在累倒的空隙創作自己作品;二是靠接不同類型的自由工作,但收入不穩定。年輕創作人主要靠參加比賽獲得開拍資金,但資助名額和比賽機會不多,就算有資金資助,獲批的預算也不多。這次入圍國際電影節的短片是周文傑獲微電影「創+作」支援計劃(音樂篇)資助的作品,獲批資金13萬,他自己最後再倒貼3萬。普遍年輕創作人都靠不斷搭膊頭,才擠到空間和預算拍自己的作品。「我試過有一次拍到凌晨3時,第二朝call 7時,場地在銅鑼灣大坑那邊。我就思考究竟我應不應該返天水圍,因為那是獨立製作、無錢給你claim的,我到頭來決定在拍攝場地睡覺,睡到第二朝繼續拍。 」
所以周文傑亦接拍商業製作、廣告片、拍攝劇照,他最近成功申請另一個資助計劃,獲得8萬元拍攝資金,但他已做好自己補貼的心理和經濟準備,「我要努力做更多所謂商業的工作,在那邊賺更多,然後填補將來洗凸的錢,或者不夠預算的作品,唯有這樣你才可以繼續創作囉……」但這也試過引來批評,有電影學院的師兄師姐覺得這些商業拍攝不是藝術,亦有朋友直指「為什麼你要做某些拍攝,好似好銅臭味呀」。他聽後覺得無奈,也反思,是否只有獨立作品才叫創作,而這種靠燃燒生命和熱情維生的創作又可以堅持多久。
各地創作者共享困惑 獲肯定重拾自信
在HollyShorts電影節,周文傑認識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創作者,發現他們也面對同樣的困惑。有一個同樣入圍,在美國讀書、來自韓國的女生,因為生活而接拍了30秒、1分鐘一集的直拍短劇的工作,「因為那些是很賺錢的,她為了繼續可以有錢創作,她就要做,她也不喜歡看,除了要找參考之外她自己也不會看」。美國的電影工作者分享說,荷李活工會行動後,電影行業還未復蘇,很多人都沒有工開。「也有些人要跟家人一起住,才可以繼續去拍攝,只不過他們的空間比較大。」大銀幕內雖然訴說的是香港年輕人的故事,但在那時那刻,在漆黑的劇院內,大銀幕下的人與銀幕內、地球另一端的人頓時共鳴彼此。
周文傑也從美國認識的電影人身上,學到要對自己的作品更有自信、更積極地尋求機會。「美國的其他電影人會好proud of自己入圍,影展的活動完結後,有些入圍的電影人留在場內做訪問,我覺得很奇怪,是不是我的作品不夠好?我就主動去問他們,他們說原來他們早在影展一星期前就事先聯絡了媒體、email了資料。因為對他們來說,這些國際媒體的肯定、在雜誌Variety曝光對他們的career path很重要,會讓投資者或者電影公司對他們更有信心,這也是他們的恆常做法。」
他感到很驚訝,反觀他自己只在Instagram出了一兩個貼文公布喜訊,「有朋友問我你為什麼不周圍跟別人說你入圍,你的作品在Chinese Theatre播,因為Chinese Theatre是荷李活最出名的(劇院),紅地氈、首映都在那裏播, 為什麼你不周圍跟人說」。他怕被人覺得自己很自大:「入圍而已,又不是獲獎,有什麼了不起。」但其實能夠在7000多套來自全球的作品中,成為427套入圍作品之一,入圍率約6%,也不是易事。
朋友將他入圍的消息分享給仍在讀電影的學生,變成對他人的鼓勵。「於是我又覺得,咦對喎,有很多現在可能還是很迷失的、讀電影的人,會不會都可以有少少的力量給他們繼續堅持創作,其實總有一天,可能都會被香港以外的觀眾看到自己的作品。 」
畢業頭一年,當他報鮮浪潮落選、報比賽無回音,他也曾質疑自己是否不懂得創作、不適合創作?問了自己很久,但他發現比起失去安穩,原來自己不寫故事,會更加不開心。這次入圍電影節,來自國際評審的肯定,也算給了他很大鼓勵,似乎原來自己的作品也不錯。而想令自己繼續進步,就是他此刻想繼續創作的動力。「我不知道,可能到我40歲就另一件事。但我現在還覺得可以做多少就得多少,因為我還有很多故事想講,就要不斷提醒自己去繼續燃燒這團火。」
文˙ 朱琳琳
{ 圖 } 廖凱霖、受訪者提供
{ 美術 } 張欲琪
{ 編輯 } 梁曉菲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