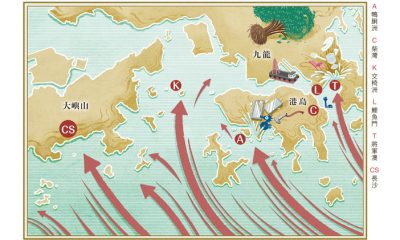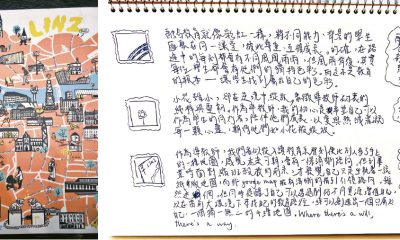副刊
星期日現場:簽證、審查與理想之間

【明報專訊】回想起去年夏天,我開始為申請美國的國際關係碩士課程着手準備。白天上班、晚上備考,撰寫入學自述時不得不反思自身的過去與未來、理想與自我懷疑,跟自己展開了一場赤裸的「靈魂拷問」。曾以為這是入學路上最困難的關卡,沒想到竟是自己最有控制權的部分。時間回到上周,幾乎每天都有美國學生簽證的新消息,一則比一則教人焦慮。通訊群組內,來自世界各地的「準同學」討論此起彼落,我們這群尚未踏上美國國土的海外學生,忽然在國際政局的漩渦中,提早上了第一課國際關係。
我對國際關係的興趣始於初出茅廬時進入新聞界,機緣巧合下加入了國際新聞組,其間有幸跟世界各地的專家、社會運動及倡議者交流。我對美國與亞洲政治尤有興趣,未來期望投身國際組織,參與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與倡議工作,而碩士程度的專業知識和研究技能可謂不可或缺。美國一直是我的首選,除了課程重視數據分析,當地亦是眾多國際機構與智庫的所在地,能在「權力中心」第一線觀察與學習,是無可比擬的機遇。
3月,我獲錄取進入華盛頓特區一個頂尖的國際關係碩士課程。喜悅仍歷歷在目,但陰霾早已悄然籠罩──當時正接連傳出撐巴人示威學生領袖被捕、面臨驅逐出境的消息。早於1月政府換屆,美國總統特朗普即簽署行政命令,要求聯邦機構加強審查學術界的「反猶言論」,特別針對外籍學生;隨後啟動「抓捕並吊銷」(Catch and Revoke)計劃,以人工智能審查社交媒體,撤銷被認為有「親哈馬斯、反猶太」傾向人士的簽證,又曾大規模取消國際學生簽證,引發訴訟潮,直至4月底宣布恢復數千學生的簽證註冊。5月,聯邦政府一度取消哈佛大學招收國際學生的資格,震撼學界,最終在法院頒令下暫緩,預料圍繞國際學生與學術自由的司法戰將接踵而來。
單是過去一周,新聞就密集得讓我恍如重返新聞編採室。美國國務院就以擴大社交媒體審查範圍為由,暫停全球學生簽證面試,隨後又宣布將積極撤銷中國學生簽證,並加緊審查來自中國內地及香港的申請。就在同一周,我也收到學校發出的I-20表格(申請F-1簽證所須文件),在準備預約簽證面試之際,撞上這場政策急轉彎。至今情况懸而未決,未知應否繼續住宿與辭職安排,所有計劃彷彿被按下暫停鍵。儘管學生簽證與貿易無直接關聯,不少分析將此舉與中美關係掛鈎,或對貿易談判帶來影響。學生在無從選擇的情况下猶成政治籌碼,受影響的卻是實實在在的個人命運與理想。
赴美讀書=自願放棄政治權利?
國務院暗示簽證面試暫停屬臨時安排,「不太可能持續數星期或數月」,但重要的是新政策能否提供清晰界線。我即將入讀的院校有定期舉行網上會議,向國際學生交代最新情况和建議,並坦承有學生或教職員受此前簽證取消影響。校方提醒我們注意社交媒體言論,並避免在美國參與政治行動(Political Activism)。這種似曾相識的論述令人不禁自我審查,也讓我反思過去任何涉及政治行動的言論會否成阻礙。有時我會掙扎,此時赴美讀書,是否等同「自願放棄」政治權利?
我所報讀的課程以國際化為傲,國際關係碩士亦自然不乏對中東政局深感興趣的人,如今卻不得不重新思考,在這樣的政治氛圍下,我們是否仍能自由討論與研究這些議題?我看到有歐洲學生因為擔心自身對中東的研究興趣,而考慮轉往歐洲升學。在種種未知與焦慮之中,學生之間只能互相扶持,在通訊群組內互通消息、彼此打氣,更像是一個臨時的支持網絡。
即使最終獲得簽證,是否能順利完成學業、平安畢業,仍是未知之數。儘管如此,目前我仍計劃前往美國讀書,並渴望在美汲取經驗,加入國際組織,參與全球發展與倡議工作。在日益高漲的反移民情緒下,這條路看來將愈走愈艱難。但如狄更斯在《雙城記》所寫:「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正是在這個急速改變、難以預測的局勢下,才更值得在最前線學習和摸索前路。想起早幾天參加獎學金面試,對方問起我的簽證進度,只好苦笑道:「見步行步。」
文˙Lisa
編輯˙王翠麗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