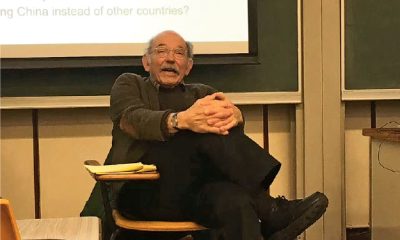副刊
星期日文學‧香港流行曲如何踏上本真之路(上)——廣東歌本質考

【明報專訊】都說香港流行曲正在復興。回顧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樂壇盛世,它生產過無數「叫幾百萬人流淚過的歌」:為了迎合最多聽眾,讓人人得以在卡拉OK代入經歷,這些歌盡可能抹掉創作者的個人經驗,提煉成大眾情感的最大公約數,代價則是其呈現的眾生面貌難免蒼白和單一。若說此城在醞釀新的流行歌,那它到底是老調重彈,抑或正朝向一種更具血肉的新形式?
本真性(authenticity)是流行音樂研究的核心概念,簡言之就是要求音樂「真率而誠實」。這概念直觀而含糊,無論粗獷不加修飾的Sex Pistols、追求玄奧創新的Pink Floyd、用民謠裎露人生的Joni Mitchell、揭露社會真象的Marvin Gaye,雖作風殊異,但一律可被視為本真的藝術家。或曰文化工業的「真」不過是資本家製造之假象,但這卻是流行曲弔詭之處:因它的魔力源於表演者的人格魅力,愈認真的樂迷,不免愈竭力追求原真感受。1965年卜戴倫在新港音樂節「插電」演出,被民歌界視為背叛,認為他走上搖滾明星的虛榮道路;2016年他榮膺諾貝爾文學獎,《紐約時報》卻發文稱頌他是媲美惠特曼的「一把本真美國聲音」(an authentic American voice)。本地最接近的案例,大概是走紅時被指「搖滾叛徒」的Beyond了;他們後來能恢復名譽,登上殿堂,也歸功於反璞歸真的〈光輝歲月〉和〈海闊天空〉。可以說,本真抑或虛矯,往往是評價流行音樂人時難以迴避的標杆。
那些流行音樂史冊上不朽的名字,往往能夠包辦曲詞,「用作品說話」——畢竟創作此一行為本身,是「真率而誠實」的最低門檻吧。按此標準,大部分香港歌星的本真性着實成疑。對此,我們慣於歸咎樂壇商業掛帥。不過,若細心思考「廣東歌是什麼」這個命題,或能從另一角度看待它的優缺——既然Cantopop的獨特面貌由廣東話塑造,那它的「結構性問題」,或多或少亦因我們母語的特性而起。
聲調枷鎖與代言模式的局限
眾所周知,粵語聲調多變,入詞極難。C Allstar的〈差詞〉道盡了歌手欲從事創作時之困境:「粵語有九聲容易拗音,唱七八九要好小心」,是故專業填詞人為歌手代言的傳統,一直根深柢固。50年間,數代大師把填詞技藝千錘百煉,確是一項文學成就,卻同時使它變成一座難以踰越的大山。事實上,自許冠傑和Beyond以後,1990至千禧年代幾近出現一段「詞曲全創作歌手」的空窗期。當年王菀之出道,林夕見她的詞沙石較多,拔刀相助填了驚世駭俗的〈畫意〉,此後Ivana果然減少親自操刀;類似情况也見於近期林家謙身上——誰叫林夕把〈某種老朋友〉寫得那麼絕呢?成也粵語,敗也粵語,「代言傳統」雖成就了歌詞藝術,卻也造成廣東歌的根本缺陷。黃偉文曾慨嘆:他和林夕「兩個人寫出600萬人心聲,是一種悲哀」。當歌手們未能我手寫我心,呈現紛陳的個性和世界觀,這樣的樂壇與本真確有一點距離。
填詞人代歌手言,等同一人分飾多角。當與歌手性情脗合,出來的作品無疑能「人歌合一」,像林振強、鄭國江、潘源良等人與林子祥的合作,就擦出了大量火花。試問像「途人路上回望我,只因我的怪模樣,途人誰能明白我,今天眼睛多雪亮」這樣的歌詞,有誰唱起來比阿Lam更具說服力呢?董啟章在小說《天工開物.栩栩如真》中這樣形容林的歌:「一個青年男子所需要的一切感情元素,都已經包含在內。熱情,孤傲,狂放,溫婉,理想高遠,薄名寡利,異域風情,古典情懷,也一一包容,那幾乎是一種情感教育」,如此的音樂似乎已很接近本真境界。1980年代不少實力派「性格歌手」如盧冠廷、夏韶聲、葉德嫻、劉美君,也是循這種模式操作。但即使這些唱將音樂風格強烈,各有一開腔便道盡平生滄桑的能耐,也端賴詞人為他們的歌勾出靈魂。詞人特別用心為他們填詞,大抵因為那是流水作業生涯中可供喘息的創作空間。聽〈三人行〉、〈你漂亮的固執〉、〈當天那真我〉、〈我要〉,樂迷所窺見的本真,更可能是林振強本人特立獨行的自我——演唱者只是詞人的「另我」(alter ego)而已。
何况有時代言只是幻象。千禧年代藉此模式大獲成功的歌手,首推楊千嬅和陳奕迅。楊千嬅早年獲人山人海襄助監製,復有黃偉文和林夕為她度身訂做,前者從動漫和藝術電影借題發揮(〈新世紀福音戰士〉、〈8步半〉、〈野孩子〉),後者則融化佛理和亦舒小說(〈電光幻影〉、《Unlimited》大碟),為她的歌曲添上知性。陳奕迅固然演繹出色,但也得力於詞人為他寫下金曲無數。從早年的年輕人心聲(〈我的快樂時代〉),到踏入成年對物質生活的反思(黃偉文「美酒、跑車、相機、金表」系列),以至對情感本質和生存狀態的領悟(林夕佛偈式的〈一絲不掛〉、〈不來也不去〉、〈任我行〉),他的歌彷彿陪伴一代人成長——套用董啟章的話,陳奕迅的歌正是不少八九十後聽眾所接受的「情感教育」。但反過來,歌手真的相信自己所唱出的話嗎?只有明瞭這套代言模式如何操作,才可理解近年為何有些聽眾對二人失望——他們大概是醒悟了一直以來從偶像作品中所體驗的「本真」,原來只是流行工業底下的一場誤會。
口語成見、敘事難度與
生活質感之缺失
廣東歌尚有一項特色,使它在本質上難以呈現真切的生活質感。〈差詞〉正好也觸及這一點:「粵語分書面口語好麻煩,用晒啲口語又好似好唔慣」、「用粵語嗎?太粗鄙啦」。
但香港流行曲好像本來不是這樣的:許冠傑不是寫了〈賣身契〉這種活現庶民生活的歌嗎?鄭國江不是也填過「鹹魚白菜也好好味」般雋永的口語情詞嗎?就此,詞評人黃志華曾提出一個論點:廣東歌在發軔之時,一直存在「俚俗詼諧」和「雕琢綺麗」兩大頑固傳統,前者(像〈賭仔自嘆〉)雖在市井流行,卻被視為難登大雅之堂。這種「母語自卑感」說來話長,與當年知識分子的大中華情結和港英政府的教育語言政策不無關係。許冠傑雖憑藉大學生身分和洋化曲風讓「鬼馬歌」升了格,但畢竟已是尾聲。他在1983年轉投新公司推出《新的開始》大碟,銳意把口語歌「雅化」,如把貓王Elvis Presley的In The Ghetto譯成悲天憫人的〈木屋區〉,卻叫好不叫座;他其後故技重施,推出〈潮流興夾Band〉等,反而顯得與潮流格格不入了,這也代表廣東歌全面進入「用粵語演唱語體中文」的時代。
日常口語在廣東歌的缺席,大大削弱它還原生活本真的功能。尋常的生活細節,當然用口語表達才傳神吧。且看朱耀偉和黃志華在《香港歌詞導賞》和《香港歌詞八十談》精挑細選的一批歌詞:〈找不著藉口〉、〈最愛是誰〉、〈細水長流〉、〈再見二丁目〉、〈囍帖街〉等,可見粵語歌詞的強項在於內在心理的幽微刻劃,多於外在現實的反映。最常見是風雨陰晴等自然景致,卻不定位於具體都市空間;人工場景像「倚窗看門外暗燈」、「煤氣燈不禁映照街裏一對蚯蚓」,又活脫脫是音樂錄影帶中刻意佈置的廠景。出外景又如何呢?林夕曾談及〈約定〉那「微溫的便當」是他在台灣的個人經歷,這細節無疑淒美而不突兀,卻大抵出於異國情調,換了是地道的「飯盒」,甚至更落實如「叉雞飯」,一入詞便勢令樂迷難以適應了。即使社會題材如〈囍帖街〉和〈花落誰家〉,前者黃偉文寫實景之時,也免不了一番詩意提煉,因此才有「階磚不會拒絕磨蝕,窗花不可幽禁落霞」之警句;後者林若寧容讓醜陋現實(「石油站」)入侵詞作時,也只是淺嘗輒止,一到副歌便回到「當櫻花迫於遷往悄靜月球」的優雅比喻去了。
「主副歌結構」(verse-chorus)是廣東歌的定式。主歌的寫景總是功能性的,為鋪墊副歌情意所服務,並常披上一層唯美面紗,力求不要暴露太多現實痕迹(追根溯源,或是受中文詩詞傳統影響,如婉約派宋詞);副歌則十居其九是直接情感傾瀉,並重複詠唱。對副歌的重視,是廣東歌要求字字協音之不成文規定的產物:為求協音,在每段副歌填上相同的字乃最省時之做法;至卡拉OK大盛,能讓K迷宣泄的情緒高潮,更是兵家必爭之地,難怪林夕也自言「寫hook line」是他花了多年才煉成的秘技。正因如此,香港流行歌本質上就是「抒情曲」(ballad),缺乏讓「敘事曲」發揚光大的土壤,像Bob Dylan、陳昇或五月天某些作品長篇累牘地說故事、文字不多重複的風格,向來鮮有出現(林振強〈笛子姑娘〉和〈薩拉熱窩的羅密歐與茱麗葉〉只屬異數)。英美故事性歌曲裏的凡人群像:像Bruce Springsteen歌裏那取得工會證後便匆匆帶着懷孕女友到法院註冊結婚,翌天去地盤打工的男子;Pulp歌裏那躍躍欲試窮人生活的聖馬丁女生,和帶她逛超市打桌球的寒酸小子;Sam Fender歌裏那剛過17歲生日,卻目睹母親無力地陷於一堆救濟部門信件的大男孩,那是一種廣東歌難以提供的逼真。
口語、細節、故事,三者雖無必然關係,卻環環相扣,是生活質感之所在,卻是廣東歌傳統所缺的板塊。有關語言特質如何決定文體取向,林夕早年曾寫過一篇〈一場誤會——關於歌詞與詩的隔膜〉,道出詞人不少隱衷。他指出:詞不同於詩,詩可以作理智冷靜的觀察,詞卻是歌者向聽眾直接傾訴,而傾訴的聲音不利於純意象鋪陳:「詩可以並列或加插一些人名地名,但歌詞要唱太多硬性資料,便不倫不類」,「有些東西是不宜入詞的,資料又如何感性地唱出來呢?」「不宜入詞」四字,彷彿成了詞人的緊箍咒。曾有一首陳奕迅的歌,demo原詞是抵死啜核的〈當柴灣愛上荃灣〉:「由柴灣返番荃灣終站,付了車資歸家太晏,冇瞓到又要上班」,令城中不少情侶深感共鳴。可是待唱片正式推出時,卻換成含蓄的〈貝多芬與我〉,大抵是唱片公司以為那麼直白的歌詞不配合紓緩的旋律吧?至於由陳詠謙所填、曾被網民口誅筆伐的一句「我現時自己肯做飯」(〈別來無恙〉),其「死因」眾說紛紜(如有說年輕人未聽過「做飯」一詞),但聽眾對生活不應如此坦露入詞的成見根深柢固,相信也是其一吧。
兩場運動、三隊組合:
艱苦的奮進
對於生活感之缺失,相信創作者也深知其弊。歷年出現的多番潮流,像城市民歌、歌手自傳歌、樂隊潮等,均反映作詞者不滿現况,力求用活的語言來呈現人生,而不跌入鄙俗詼諧的窠臼。其中兩次由詞人獨力發起的運動尤其意味深長:1980年代初盧國沾高舉「非情歌運動」旗幟,更試圖把戰線延伸至情歌(他稱之曰「愛情與麵包」),市場卻反應欠佳;千禧年初黃偉文號召「新廣東歌運動」,其第一擊〈你唔愛我啦〉則被網民選為「十大西歌之首」(「西」即騎呢惹笑之意),足見樂迷口味牢不可破。
達明一派、Beyond和軟硬,可說是箇中異數。達明一派的案例,印證了代言模式仍有可為,但只有在特定條件下才能發揮最大威力。首先,樂隊本身在音樂上具強大創作力,且每張唱片均目標清晰,故歌詞無論出自陳少琪、潘源良還是周耀輝手筆,均能貫徹統一主題:如《石頭記》的孤獨眾生相、《我等着你回來》瀰漫對香港前途問題的疑惑,都可視作「概念大碟」,更遑論成就最高的《神經》了:這是一張籠罩空蕩廣漠氣氛的「聽覺公路電影」,一闋於百姓瑟縮諸神廝殺之時代中,流浪者被放逐荒土、與噩夢展開無止境掙扎的史詩。其次,他們不滿足於樂隊常見的口號式吶喊,反而致力用作品說故事、繪眾生:無論早期作品的邊緣青年(無視警車響號的「馬路天使」、「美好新世界」內的高買者、沉溺迷幻感覺的「溜冰滾族」),還是其後的社會群像(躲藏行人隧道執著刺刀的精神「崩裂」者、困於性別定型的「神奇女俠」、「沒有張揚的命案」裏被大眾埋葬的社會先驅),都引領聽眾從流行夢工場走向赤裸裸的現實世界。當然,諸因素中最重要的,還是歌者本身在社會和性別運動中身體力行、言行一致。
Beyond之例,則說明能包辦曲詞之可貴。他們芸芸作品中,若論文采斐然,當推劉卓輝所填的家國隱喻巨構如〈大地〉、〈長城〉、〈農民〉,然而最廣受傳誦的,反而是那些文筆稍為幼嫩,卻由他們親自作詞的歌。像〈光輝歲月〉和〈Amani〉,動人之處來自歌者的生命體驗:只因Beyond曾親赴非洲採訪,更在大紅大紫之際冒險改變歌路,竭力宣揚和平,它們才比其他歌手的反戰歌具說服力。同樣地,若非樂隊不甘屈服主流娛樂圈規則,毅然出走日本追尋創作自由,黃家駒更間接因此悲劇身亡,〈海闊天空〉那雪地漂泊之畫面又怎能如此震撼人心?如今重聽早期的《亞拉伯跳舞女郎》大碟,其野心除了把中東音樂的Phrygian音階融入主流曲式,也見於其建構敘事世界的嘗試:主人公遠赴大漠尋找「東方寶藏」,卻陷於「沙丘魔女」誘惑,最終只能嗟嘆「新天地」幻滅──這分明隱喻了他們背負「搖滾叛徒」罵名,試圖深入建制改變現狀之困局。這種用生命寫的故事,決非代言式製作所能承載。
至於軟硬,指出的是另一種可能性:欲擺脫粵語聲調的桎梏,說唱(rap)誠然是可行之道。事實上,一張《廣播道軟硬殺人事件》,所包羅的社會內容便差不多超越同代所有歌曲的總和:愛滋病危機、交友電話潮流、蘭桂坊人踩人事件,還有中國在市民生活無處不在的影響力。無奈礙於其喜劇形象,他們的歌當時仍被視為許冠傑式鬼馬歌之餘緒,未能打破部分聽眾對口語入詞的成見,但無疑已為其後的說唱者(如LMF)開闢了道路。
以上簡述了八九十年代本地樂壇朝着本真之路的艱苦奮進。待千禧過後,樂壇生態丕變,始迎來了新的生機。
(隔周續)
文•潘拔
美術•劉若基
編輯•鄒靈璞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